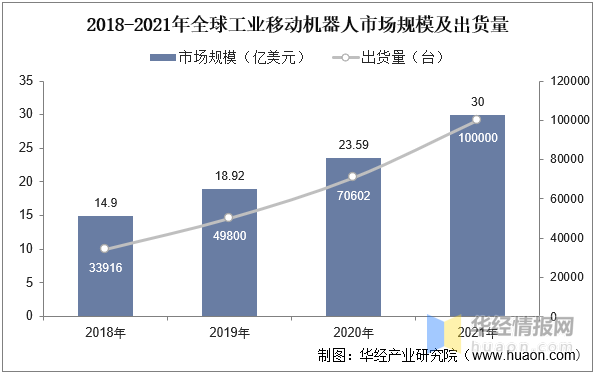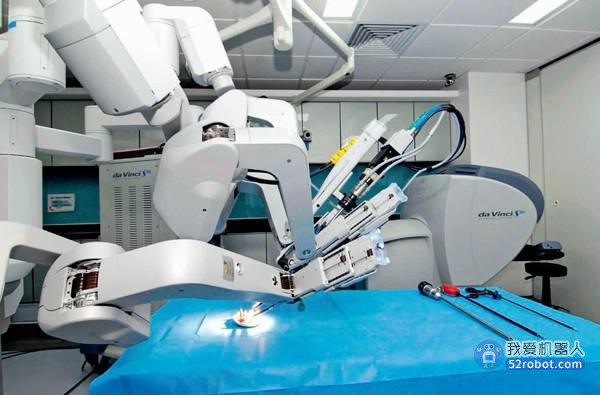机器人女友要来了?一百年前就有体贴的“声控先生”
近来,网上流传一种说法,“马斯克研发‘猫女’机器人,或将在三年内量产”,与之相配的还有两张马斯克与“猫女”机器人接吻的图片。据称,“猫女”机器人可永葆青春、美丽、性感,会做饭、不吵架、不离婚、不分财产,还会生孩子。


这些都是假的!
如此一来,浪漫的机器人女友将照进现实。姑且不论这背后的女性凝视,该说法很快被证明为假消息。

在TED创始人Chris Anderson的访谈中马斯克表示,他将生产「猫女」机器人。
尽管“猫女”机器人的研发和生产只是谣言,但一百年前,人类的确打造出了六款外表温顺、任人摆布的奴隶机器人——黑脸机器人拉斯特斯和它的“家人”:“声控先生”、“卡特里娜·范·声控”、“光控先生”、“威利·声光”与“小电子”。——它们的使命不过是向当时的美国中上阶级白人家庭传播机器人奴隶理念。
而这只是美国文化关于机器人想象的一环而已。长期致力于文化史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加州大学美国研究系教授达斯汀·A·阿布内特,基于跨学科视角,引入思想史、文学、电影和电视等资源,追溯了美国文化中机器人观念的历史。

达斯汀·A·阿布内特(Dustin A. Abnet),加州大学美国研究系副教授,历史学家和美国研究学者,专业领域为文化史和知识发展史,科学与技术史。
让我们从奴隶机器人开始,看看美国人是如何想象机器人的,在机器人观念的变迁中思考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
1
“声控先生”:
一百年前的机器人“伴侣”
20世纪30年代,声控和光控技术兴起,机器人制造商制造出能被消费者便捷控制的机器人。期间,西屋公司打造的六款男女机械人最为耀眼。
这六款机械人——拉斯特斯和它的“家人”:“声控先生”“卡特里娜·范·声控”“光控先生”“威利·声光”和“小电子”——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处不断表演。无论这些机器出现在哪里,都吸引了大批人群,报纸也大肆渲染。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标志。
《无线电工艺》杂志中印了两张拉斯特斯的照片,庆祝电气制造取得了惊人进步。而作者则给它起了个外号:“拉斯特斯·机器人先生,世上最像人的机械人。”人们在这些文章的影响下,越发认为机器人是这些机器,而不是恰佩克的生物性人造人。
拉斯特斯既不是西屋公司的第一台机器人,也不是西屋公司最受欢迎的机器人,但它是该公司生产的唯一一台黑脸机器人。他的名字出自黑人戏,外表温顺,毫不掩饰地热衷于取悦他人,是个彻底的奴隶。拉斯特斯清清楚楚地奉上了一种控制机器和黑人身体的幻想。
“声控先生”则拥有白人男性形象,即使柔弱的女人也能控制这种强壮的机器人,因为声控装置不仅仅是一台机器,它还是一个“电动人”和“机械奴隶”。
在关于“声控先生”的想象中,男人和女人除了思考之外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给“声控先生”打个电话,问它问题,再下达命令,“声控先生”就会取物品、制造机器文明所需的无数物品、打扫街道、洗衣做饭和挖沟渠……它不会像一般人那样争吵、无礼或拖延。“声控先生”比人类劳动力更优越;监管员和工程师应占据主导地位;而人们则生活在一个闲暇世界中做着更有意义的工作。
更进一步地,在关于“声控先生”的想象中,他具备了成为“理想丈夫”的许多条件,俨然一个性转版的“猫女”机器人——帅哥机器人老公。“声控先生”将总是陪伴在身边,这个男人好得不得了,能完美地模仿出女性最爱的偶像派男演员或电影明星的样子,不管是金发还是黑发,下巴上留着小胡子还是刮得光溜溜的,女性的心中所愿都能实现。

图中是“赫伯特·声控先生”和一位西屋公司工程师的妻子,后者对前者爱护不已。女性对声控先生的兴趣常常是西屋公司和评论者强调的主题,以此来讽刺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最初的图片说明将这台装置称为“罗密欧·声控,理想的情人”。图片来源:乔治·林哈特(George Rinhart)/ 考比斯·盖蒂图片社(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不过,这些美好的幻想都被美国的大萧条所终结。在大萧条时期,“声控先生”们给民众带来的只有痛苦。
2
帮助处理人类紧张关系:
美国机器人想象背后的文化逻辑
“声控先生”只不过是关于机器人的一种想象,而历史地看,美国文化中的机器人先后出现了多种形象,从美国早期的奴仆想象“自动机”,到机械化时代的反抗者想象or消费机器“机器人”,再到后工业时代的卫士想象“赛博格”,机器人观念不断发生变化。
美女机器人令人着迷,而与此同时,在这两百多年来,美国人也因为机器人而感到恐惧。
《机器人简史》一针见血地指出,机器人更像是一个多面角色或一面镜子,人们用它来处理社会中久远的紧张关系,它也反映出了特定的社会文化逻辑。
依赖机器人的介入,美国人得以和现实达成和解,毕竟现实通常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无辜和仁慈。
例如,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而自动机想象又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奴仆。又如自从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文化一直歌颂自力更生,在劳动中获得成就以及自我认同的男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独立不过是幻想,意义更是奢望……
于是,性爱机器人以及其他人化的机器应运而生,在这些对机器人的幻想中,美国人既驯服了机器,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驯服了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从而在否定他者的过程中找回自身“活力”。

鲁迅笔下的阿Q也是通过否定他者找回自我。
和美国表面上声称的民主形象相反,在大部分美国历史中,机器人融合了中上层白人男性驯服他者身体的幻想,以及驯服现代性中失控的机器的幻想。
这种幻想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想象和现实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身份认同的核心不再是工作而是闲暇,异化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在工作时充当机器人,在闲暇时作为人而存在。人们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消费主义社会中每个人似乎都是快乐的人造机器人。
这种模糊了人和机器人的观点,以及美国人生存处境的恶化,又反过来使得边缘群体“物伤其类”,用虚构的机器人来批评对被征服者的物化。
于是,在一些机器人反抗的故事中,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欢乐和希望,因为它给人以建立一个没有历史上的歧视、暴力与压迫的新美国的希望。

梦奈(Janelle Monáe)在专辑《大都会——第一组曲》中呈现了幻想中的自我,一位来自未来城市“大都会”的人,她的躯干被肢解,露出了电线,她留有标志性的黑人发型,这身打扮象征着“真正的”黑人生活在人造的白人世界中的危险。梦奈通过将自己改造成反抗的机器人来批判对他者的物化。
《机器人简史》给予我们两个看待机器人的视角,一个是作为机器化的人,例如予取予求的机器人对象,借此将控制、排斥和对抗其他群体的努力合理化。
另一个是人化的机器,例如各种家务机器人、Siri等数字助手,它们提供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承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然而人被机器化的困境却与之共存,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
该书提醒我们,放眼美国两百多年的机器人历史,机器人诞生之初不过是一个奴隶制幻想,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机器人又激发了人类对身份认同中唯物本质的接纳,逐渐从控制的象征转变为自由的象征。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